黑市交易人体器官像卖白菜,富人花钱续命
- 2020-05-29 11:36:52
- 来源:
- 编辑:51温哥华小编
- 0
- 0
去年,英国“死亡卡车案”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39具尸体是在冷藏车中被发现的,所以当时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贩卖人体器官的黑暗组织所为。
其实,如果对器官买卖稍有了解,就会知道这种猜测有多不靠谱。
或许正是因为大部分人都身处光明之中,对那个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既恐惧又陌生,才生出这类的怀疑。
今天分享的《人体交易》,就是一本关于器官贩卖的书。
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中的残酷和不幸,没有半分道听途说和猎奇,而是作者花费了十年时间,走访最黑暗的全球人体市场后,亲自记录下来的。
在市场上,人体器官就像白菜一样被人买卖,每桩交易的背后,都藏着血淋淋的残忍真相。
肾脏村
2004年,印度洋发生海啸,夺走了20多万人的生命。
灾难过后,很多人都向受灾地区奉献过自己的爱心,我也是。我们都以为,在世界各地的援助下,灾民们很快就能重建家园,找回往日的安稳与宁静。
但现实并非如此。
经过政府官僚的层层克扣,国际社会的支援物资已经所剩无几。灾难过去两年后,位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灾民依旧一贫如洗。
有人从这场灾难中看到了商机,他们就是游走于医院和黑市的器官掮客。
掮客们瞄准了这些生活艰难的难民——他们虽然没有钱,但至少还有一个可供售卖的肾脏。

在这里,几乎每个成年妇女的腰上都有一条弯曲凸起的疤痕。
然而,她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卖肾而变得容易些。
灾民罗妮的女儿嫁到婆家后,因为家里无力置办嫁妆,天天被丈夫殴打,痛苦不堪之下喝了杀虫剂自杀。
为了筹到女儿的住院费,罗妮经村里卖过肾的妇女介绍,认识了一个肾脏中介。对方承诺会付给她3500美元,术前先预付900美元,余下的在术后结清。
在移植手术前,她提供了自己的血液和尿液去配型,配型成功后,有人会送她到金奈的一家综合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授权委员会的伦理审查,来确保器官移植手术合法且没有金钱交易。
当然,器官掮客会用2000卢比(不到30美元)行贿,所谓的审查不过是一场彼此心知肚明的过场戏。

文书下来后,罗妮的肾脏很快以“自愿捐献”的形式被移植到了买家的身上,她没有见过买家,据说是一位有钱的妇女。
手术三天后,罗妮的伤口还在不断渗出液体,医院却给她办了出院,让她回家恢复。等到一周后她再回去做检查,所有医生都装作不认识她。
那个掮客也不知所踪,承诺术后结清的钱当然也没有兑现。

罗妮知道自己被骗了,和她同样被掮客欺骗的还有33岁的玛莉佳。玛莉佳只拿到了750美元,连术后的医药费都是自掏腰包。
她向警方投诉,但警察却说,这样的话,要连她一起逮捕才行,因为她是卖方。
更糟糕的是,没过多久,玛莉佳儿子得了B型肝炎,并引发了肾衰竭,她却连肾也没法捐给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去。
在印度,人体器官是社会底层提供给社会高层的,绝对没有反过来的事。

这些踊跃卖肾的灾民并不是见钱眼开,而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一张渔网和一架三轮车,这样就能把捕捞的鱼运到市场上卖,活下去。
新形态的食人主义
在海啸难民区,卖肾是公开的秘密。
这些手术的要价是14000美元,但那些卖肾的灾民只能拿到其中很小一部分。
掮客抽取部分佣金后,剩下的都会被大交易商山卡尔拿去。每卖出一个肾脏,他就能分一杯羹。
而这条肮脏罪恶的产业链,之所以能运作这么多年,是因为无良医生和腐败警察的保驾护航,以及“受赠者和捐献者的隐私保护制度”衍生出的诱人盈利模式。
正是这个制度,让掮客们在吸完卖肾者的血后,又能在买方那里狮子大开口,捞上一笔。

院方和医生们堂而皇之地声称,捐献者和受赠者会面,会对双方造成严重心理伤害。
但真实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人类学家莱丝莉·夏普曾在《奇异的收割》一书中讨论过美国的遗体捐献制度。
她写道,匿名制度是近年才出现的医学伦理,从前医生会主张把捐赠者介绍给受赠家庭,这样双方可以分享病例,提高手术成功率。两个人也会因为生命的延续,产生一种“生物感伤”。

而现在,器官移植的需求,已经近乎于一种新形态的食人主义。
一些无良医生正在给走向死亡的患者,画下美好的大饼——别怕,只要你有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一定有个“穷人”,会“帮助”你活下去。
毫无疑问,等待移植的名单会越来越长,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寄希望于器官移植给他们带来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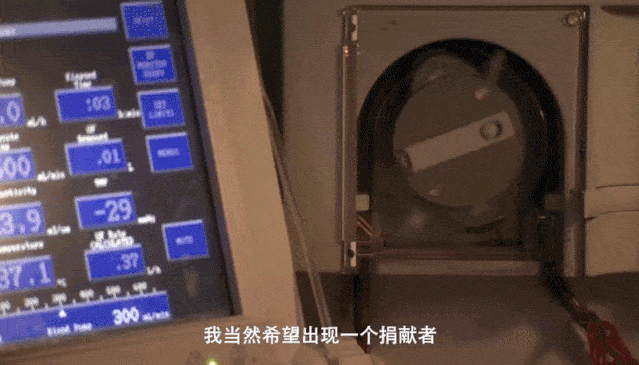
但实际上,移植手术成功后的生活,并不是浴火重生,失去的健康在术后可能只会恢复一小部分。
术后,患者不仅需要服用大量抗排斥药物,还可能面对器官再次衰竭的情况。到时,他们只能想办法再去买一颗器官。
器官移植和抗排斥药物的发明,在创造“医学奇迹”的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衍生出器官交易这个以命续命的残酷世界。
卵子采购天堂
在欧洲与亚洲的交接处,有个叫塞浦路斯的小岛国。
在不大的国土上,遍布着数百家生育诊所,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卵子被取出,植入远道而来的女性客户的子宫内。
生育旅游,是这里的特色产业。
在塞浦路斯,每50个符合捐卵条件的女性中,就有一个会贩卖自己的卵子。
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14000。宽松的法律,是这里生育产业的温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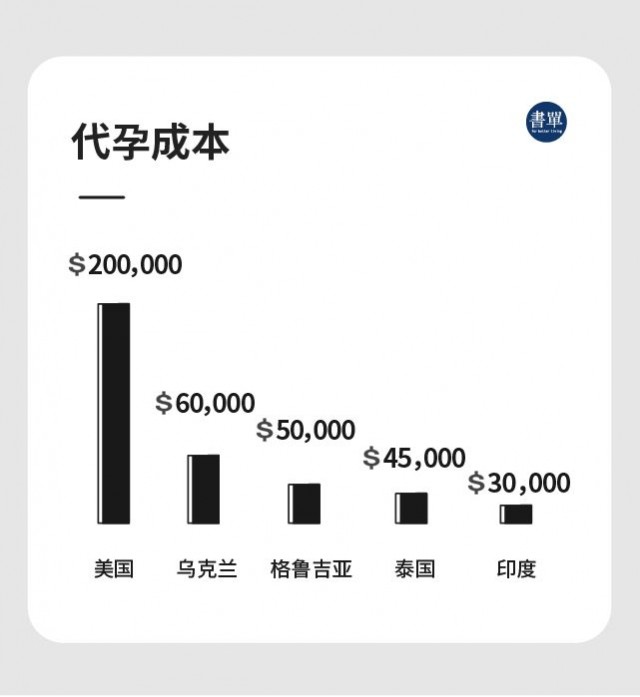
根据欧盟法律,欧盟国家(如塞浦路斯)必须“尽力”确保人类卵母细胞的捐赠是自愿且无偿的,但允许支付补偿金,弥补薪资损失和交通费。
借助“补偿和经济获益”的暧昧界定,“供货商”和顾客们很容易规避法律的限制。
对于这条如同废纸一样的条例,生物伦理学家麦基曾经讽刺道,领养猫咪的难度还比采购卵子高一倍呢。
来此卖卵的多是东欧国家的贫困女性移民。在塞浦路斯,共有3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摩尔多瓦人和罗马尼亚人,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在卖卵。
由于皮肤白皙,教育水平高,她们的卵子很容易就能推销给西欧的顾客。
招募捐卵者和售卖卵子的广告也随处可见。
点开生育诊所的网站,就可以看到大量捐卵者的信息,像超市货架的上的商品一样,注明国籍、年龄、身高、血型、学历、发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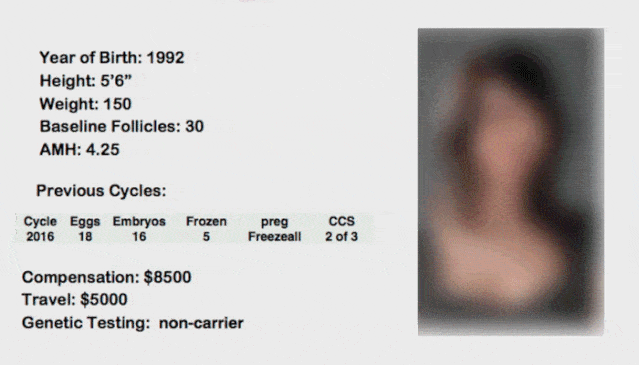
比如编号17P,乌克兰人,身高175,体重59,血型B+,发色栗色,眼睛棕色,教育程度大学毕业,职业艺术家,年龄23,抵达日期2月2日至10日,预计取出日期2月5日至7日。
这些信息,看似能给来此购卵的人以安全感,实则不然。
为了榨取更多利润,这些诊所常以过度刺激的方式,让捐卵者排出更多卵子,再将这批卵子卖给多位客户。
如此一来,每一次卵子周期的利润就会翻倍。
但过度刺激不仅会对捐卵者的健康带来很大损害,卵子数量的激增也会造成质量的下降,受精成功率就会大大降低。
捐卵虽然不致命,却是一种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且伴随着手术风险。

捐卵者需要经过至少两周的荷尔蒙刺激,然后才能动手术取出卵子。注射荷尔蒙所引发的并发症不但痛苦万分,且可能危及性命。
也许有人觉得,让这么多女孩趋之若鹜,甘愿承担生命风险的卖卵,酬劳一定很高吧。
不,卖一次卵的出价,是1000至2000美元,只够她们生活几个月。很多女性卖卵,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或者赚取回国的路费。
和那些印度难民安置区的人一样,她们之所以出卖自己的卵子,并不是为了满足物欲,也不是为了赚大钱,而是因为她们太穷了,穷到活不下去了。
地下血液农场
在印度边境城镇哥拉浦,一名虚弱的男性向一群在田边休息的农夫求救。
然而这群农夫却不愿意伸出援手。
因为他皮肤苍白,两条手臂上布满了针孔,看起来像条“毒虫”。
直到他解释说,自己没有毒瘾,这些针孔是被人囚禁起来抽血卖钱留下的,农夫们才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打电话报了警。
就在田边不远处,有一间用砖块和锡料搭的简陋小屋,从外面看起来并无异常,但里面却比地狱还要可怕。
过去的3年,那名男子就是被关在这里,被不断地收取血液。

和他一同被囚禁的还有5名男性,警察破门而入时,他们正躺在木板床上,瘦骨如柴,目光呆滞,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手臂上插着针头,血液正顺着塑料管缓缓流入地板上的血袋中。
每个血袋都贴着官方认证的当地血库的贴纸和中央监管机构的条形码和封条。
这并不是唯一的监牢,之后警察又在另外五栋小屋内解救出17名受害者。
每周至少两次的抽血令他们虚弱不堪,健康成人每100毫升血液就有14至18克血红素,而他们平均只有4克。
苍白的皮肤因脱水而发皱,捏起来后会像粘土一样保持形状。
很多人已经在这个地下血液农场囚禁了两三年,能活着挨到营救,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每当有人快要死了,榨取血液的农场主帕普·亚德哈就会把他们放在公交车上载出城外,这样他们的死,就是别人的责任了。
警察找到了亚德哈的账本,上面明确记录着他把血液卖给了当地的血库、医院和私人医生,以此赚取高额利润。
这些受害者都是想要卖血的尼泊尔贫民,为了果腹,被他3美元1品脱(约568.3毫升)的价码所吸引。
更可悲的是,亚德哈是个当地很有声望的酪农,那些囚禁人的小屋,就在他的牛棚旁边,一墙之隔,一边是奶牛在产奶,一边是人在抽血。
然而,在这个文明世界的边缘,哥拉浦血液农场案只不过是众多惨绝人寰的案件中,很平常的一件而已。

这是一个个富人花钱续命,穷人拿命换钱的真实故事。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但原来以为,至少在时间和生命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但这本书让每个现代人看到,生命是有“贵贱之分”的。
活体取熊胆汁算什么,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些人在被活体取肾脏,榨人血。
就像这本书封面印的那句话:
别再提那些深山老林的食人族了,现在的人类对人肉的欲望程度,才是史上最高的。
人类对生的希望和珍视,对死的逃避和恐惧,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如今一切却变得扭曲,畸形。
当一个人生命的延续,是以伤害另一个人为代价,那“长命百岁”到底是一句祝福,还是一个诅咒?

免责声明:本网发布新闻仅为传播即时消息为目的,不确保内容准确或真实性,文章也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文章有错误或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联系邮箱:info@idomedia.ca










网友留言评论